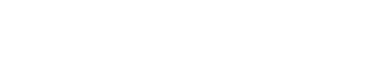中新社与法国《欧洲时报》
记者专访中国法国文学专家
——徐真华:喜欢探讨人生的文学
欧洲时报网特约记者冷语晴北京报道:徐真华,1950年生于江苏无锡,1975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后由国家派赴摩洛哥王国五世大学法国语言文学系进修,1977年返回广外法语系任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赴法国新索邦大学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研修法国现当代文学和高等教育管理。1995年至1998年在广外国家级重点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心攻读并获颁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主要著作有:《理性与非理性—20世纪法国文学主流》、《法国文学导读—从中世纪至20世纪》、《文学与哲学的双重品格—20世纪法国文学回顾》、《从广州年轻人的语言态度看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米兰·昆德拉:小说是关于存在的诗性之思》等。曾主持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20世纪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广东省211工程第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图为徐真华生活照
在徐真华的简历中,有着很吸引人的一段描述,他不仅是一位有着丰富治学经历的学者,还曾是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学术和行政职务兼顾的他,在2003年被评为广东省高等学校十大师德标兵。他说:“我最欣赏那些把文学、哲学和文化结合起来探讨人生的法国文学家。”也许正是丰富的阅历和多样化的身份,让他偏爱那些探讨人生的文学作品。
文学青年的好底子
和大多数同龄的知识分子一样,徐真华也是从工农兵学员变成了一名大学生。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22岁了。从小喜欢文学和历史的他,在学习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仍然读了很多书,小学到中学,他一直喜欢外语,爱写文章。
那个年代选大学生,不像今天的高考。考察重点是能否和乡下的农民劳动、生活在一起,有没有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是能否顺利进入大学的重要指标。“我在苏北乡下的四年,每天都和他们‘泡’在一起。过了这关,再经过大队、公社推荐到县里,上百名知青一起参加考试。”徐真华说,“当年广外(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在江苏招了18个人,其中17个是当地知青,只有我一个是从城市到苏北去插队的。”徐真华把他顺利进入大学学习,归功于幸运,归功于吃得苦和自己那篇写得还不错的考试作文。
“可能是有学英语的底子吧,我学法语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他回忆说,“那个时候,学生最怕听写了。譬如一篇两三百字的听写,大家普遍都会有三五处的错误,但我一般很少会出错。”他学法语的感受和不少从事了多年法国文学研究的老师差不多,那就是轻松而快乐,学习并不是负担,这也成为了他们能够一直在法语这条路上走下来的重要原因。
丰富的法国文学治学经历
说起学习经历,徐真华最初的感受是,上了大学,生活开始变得安稳,而最重要的体现是:能吃饱饭了。再就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原来的那些很优秀的同学,绝大多数都还在乡下种地,自己却有了上大学的宝贵机会。“我当时就非常明确地告诫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书读好。当了4年农民,终于有机会进入一片完全不同的天地,这是一种莫大的转机。”
强大的动力,加上以前英语学得比较好的基础,徐真华的法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大学毕业前就被提前选拔为出国留学的培养对象,学成归国后再留校任教。1975年,他和国内其他外语学校的几名同学,一起前往摩洛哥王国五世大学学习,那里的法国文学系全是由地道的法国教师授课。“也就是这次留学的两年时间,为我们打下了比较好的听、说、读、写的法语基础。包括我后来回
在国外留学的日子里,徐真华最大的感受来源于不同文化造就的不同生活方式。作为曾是“法国保护国”的摩洛哥,既具有浓厚的阿拉伯风情,又兼备法国文化的气质。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讲,除了中国的“母文化”和法国文化外,在这里体会到了“第三种文化”。“这段经历使我们培养出了包容、宽容和多元的文化视角。”徐真华回忆,“那个时候中国还比较封闭和贫困,人们的思想单一,穿着只有一种款式。但摩洛哥尽管是伊斯兰教国家,首都拉巴特已经比较开放。在我看来,那里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状态,虽然贫富差距仍很明显,乡下的生活也比较苦,但城市居民已经过上了不错的日子。"
从较封闭的中国前去学习的留学生们,已经在那里看到了第三国家的发展,一个全新的发展前景在眼前铺展开。除了多元文化带来的冲击外,摩洛哥的学习经历也使徐真华和他的同学们在法国文学的学习上收获丰厚,因为文学课程所占的课时比例是最大的,加上人类思想发展史和艺术发展史这类课程的辅助和支撑,使文学的内容变得更加厚重。
在国内学习时,徐真华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十八、十九世纪比较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法国文学作品,而到了国外,更多地接触到了二十世纪一些作家的作品,他的兴趣也随之转向了现代文学,因为这类作品更关注人的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更是现代气息。
“比如马尔罗,”他举例说,“我对他就很感兴趣。包括莫里亚克也是,所以十年后,当我有机会再到法国去留学的时候,把他作为了我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
现代法国文学关注“人的存在”
和徐真华年龄相仿的学者,大都喜欢经典的传统法国文学作家和作品,他认为这是源于一种相互契合的原因,“那个时期的法国文学作品关注现实,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类型,这类作品聚焦基层老百姓的生存状况,透视人的喜怒哀乐以及情感生活等。比如司汤达,他关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青年如何为自己争得地位,如何获得爱情,如何奋斗等等。这同中国解放以后几十年崇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一致的。”
徐真华认为,到了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有了比较重大的转向。虽然文学作品仍写现实,但重心却转移到关注和研究“人的存在”上来。“就像昆德拉所说,文学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因为人的存在被遮蔽了,被意识形态、被技术工具、社会的种种习俗、宗教的各种观念以及人类自身追求物质生活的目光所遮蔽。因此文学应该将这些遮蔽去掉。”
现代法国文学作品所彰显的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批评主义、新小说,荒诞派文学等等,正是要揭示人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也许生活是无奈的,但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给自己的生活创造意义和价值,也就可能会创造另一种不同的存在,而不要安于自己的“命”。
“我在和研究生讨论法国文学家和他们的作品时,比较注重挖掘他们作品背后想要传达的信息。”徐真华说,“我最欣赏现代作家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文学、哲学和文化结合起来探讨人生,这是一种超越。就像马尔罗,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更是个悲天悯人的文化哲学家。年轻时,他崇尚革命,在他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创作的几部作品中,描绘了东方民族面对痛苦和死亡所表现出的从革命中寻找尊严的强烈愿望,和对自由和平的热切追求。”
马尔罗不懈地透过文学作品的形式来探索信仰的本质和含义,表现人类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强烈愿望,并且颂扬能够战胜死亡而成为永恒的艺术创造。对于他来讲,死亡令人的肉体消灭,但艺术却可以创造出生命的永恒。
徐真华很欣赏这样有思想的文学家,他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文学作品描绘生命的尊严和自由,表达对人性、异化、生、死亡以及人的尊严等很多形而上的思考、追问和反思,这些都和中国的文学作品不甚相同。
“莫言获了诺贝尔奖,”谈到法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时,徐真华说起了莫言,“我跟学生们讨论,为什么他能获奖,学生说因为他的作品是乡土文学,反应了他生活的那片土地上人们的喜怒哀乐。但我想这个答案不全对,因为乡土文学作品很多,美国有、法国有,中国和印度也有,为什么偏偏是莫言呢?”
“也有人说因为他的作品反应了某种普世的价值,能引起人们共同的思索,这个答案也不准确,因为具有普世价值的作品也不少。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莫言的作品除了上述两个特点外,还表达了比较深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质疑精神。他对社会、对人、对人性的反思是一种呼唤,呼唤回归本源或某种意识,而不能停留于现状,应该超越这种状态,去追求一种形而上的,更加理想的状态。”
徐真华认为,莫言的作品可以引导人们去思索,就像他提到的那些法国文学家一样,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的关怀和对人性的拷问,而这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作品让读者一起高兴或落泪的教化层面。也正是这类作品,共同创造了世界文学的高峰。
文章略有删减